“龙生龙,凤生凤,老鼠的儿子会打洞”,是一曲唱不完的老调子。
持血统论,出身论,成分论的人,在中国,从古至今,总是络绎不绝的。这大概和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那种不变的世袭制度有关。皇帝的儿子当皇帝,贵族的儿子做贵族,奴隶的儿子,也就永远是奴隶了。古往今来,凡皇帝、贵族和他们的儿子,都喜爱唱这老调子,说穿了,也是维护那个既得利益的等级制度。
唯一的例外,三国期间的大政治家曹操,倒是历史上比较不大买这种老调子账的帝王,着实让人钦佩了。
当时,魏蜀吴三国首领,要论出身,吴为江东贵族,魏是中原豪强,只有刘备,是个织席贩屦的手工业者。要以今天观点,刘备应该为自己可划入红五类而庆幸的。但在汉代,他自己颇有点自惭形秽,穷酸窘迫,深感上不了台盘的。于是,总抱住皇叔这块招牌不放,到处显示他形迹可疑的贵族出身,又可笑,又可怜。所以,他一听太史慈说,孔融求他出兵,马上得意起来,“孔北海尚知世间有刘备乎”,一脸悻悻然的样子,很觉得被这位大世族看重而自豪。后来,被东吴招为驸马,也是以皇叔的身份,再去攀附江东贵族的高枝,说明他是服膺于这种老调子,而想拼命挤进贵族队伍中去的。
曹操则不然,他并不期求这种高贵身份,在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里,他只要求死后在墓碑上刻上“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”就行了。虽然作为谋略,把女儿嫁给了汉献帝,当上了皇帝的岳父大人,但他从来没有为此而自炫过。孔融在北海混不下去,跑到许都来,他也没有像刘备那样觉得荣幸,后来,因为孔融老是捣乱,便不客气地将他杀了,根本未把孔子世家当回事。其实,正因为孔融是士族的代表人物,才要了他的命的。煮酒论英雄时,曹操把袁绍、袁术、刘表之类出身名门望族的州牧,统统予以否定,倒把平民出身的刘备抬得很高。曹操的话里,多少也是含有一种对门第观念的否定情绪。
因为自秦汉以来,这种老调子使得选拔人才的圈子,越来越狭隘,进取的机遇,越来越不公平。单向选择的结果,官员的质量越来越下降。所以,对于这种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,曹操是一个具有挑战精神的人。他一再发出命令,要求各部门不拘一格地擢用人才,哪怕像陈平盗嫂受金、不干不净、信誉不佳的人,像白起杀妻求信、母死不归、贪酷可疑的人,只要有本事,就要予以使用。
曹操从他早年任洛阳北部尉起,就反豪强,蔑权贵,表明了他对这种老调子的厌恶。“造五色棒,有犯禁者,不避豪强,皆棒杀之。后数月,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,即杀之。”
后来,董卓窃权当国期间,曹操作为总策划,会盟十八路诸侯,组成讨伐联军,理所当然,他应该统帅这支队伍。因为他不仅具有组织能力,还有相当的领导能力。但是在誓师大会上,袁绍却被公推为盟主,又一次使他对于龙生龙,凤生凤论调的质疑。他是说过,袁本初“四世三公,门多故吏,汉朝名相之裔”的言不由衷的话,实际上他是不相信像这类仗着老子娘的余荫,依赖先人光荣的子弟,既非武艺高强,更非韬略出众,能够指挥这次军事行动。可曹操不过试探的话一出口,那些诸侯都是血统论的拥护者,皆曰:“非本初不可!”于是,曹操不得不把领袖的位置,拱手让给袁绍,这一方面是他的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,另一方面也是十八路诸侯所持的门第等级观念,使他觉得自己的家世无法予以相敌。正是这种处于弱势地位的逆反心理,促使他一生在反抗这种等级观。
这场讨卓行动,由于袁绍无能,袁术作乱,遂以四分五裂告终。曹操气得直骂:“竖子不足为谋!”也是对这些没有真本事的名门子弟的彻底唾弃。他在《取士毋废偏短令》里强调:“夫有行之士,未必能进取,进取之士,未必能有行也。”“士有偏短,庸可废乎!”他之所以特别强调唯才是用,不讲德,不讲资,也不讲出身和成分,是有他的针对性的。
按他的意思,如果是老鼠的儿子,有打洞之长,也要起用。他的一生中,招降纳叛,不咎既往,大胆使用从敌对阵营投奔过来的文臣武将,不可胜数。譬如他对捉住的关羽,那样地隆重礼遇,恐怕此前此后的领导人,都很少有他这样的气魄。但另一方面,他在对付皇帝、贵族、豪强和士族的代表人物,则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击。在《诛袁谭令》里声言:“敢哭之者,戮及妻子。”将袁绍、袁术这个名门望族,一点也不留情地斩尽杀绝。在《宣示孔融罪状令》里说:“融违天反道,败伦乱理,虽肆市朝,犹恨其晚。”从舆论上把这个大知识分子搞臭。在《赐死崔琰令》里说,“琰虽见刑,而通宾客,门若市人。”杀一儆百,也等于对整个士族集团的整体警告。一直到他临死前的建安二十三年,都城许昌发生一次由士族不满分子发起的动乱,他又疯狂地加以镇压,几乎夷灭了全城的豪贵。从而为他儿子接他的班扫清了障碍。
曹操对孔融、崔琰的耿耿于怀,除了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外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由于山东孔姓,河北崔姓是当时有影响的大士族。打击他们,等于打击这个阶层,也是对龙生龙,凤生凤这种老调子的否定。
但是,他绝没有想到,他的儿子曹丕上台后,强调门阀的九品中正制,所谓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势族”的老调子重又弹起。因为等级的尊卑,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。到了两晋、南北朝,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:琅琊临沂王氏,陈国阳夏谢氏,以及山东崔氏,吴郡陆氏等,就凭他们的姓氏,便是财富的象征,政治的资本。甚至北朝的一些异族君主,都想通过与华族的婚姻,来改变自己的夷狄身份。直到隋唐,门阀之风才渐渐式微。刘禹锡的诗,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,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便是一曲没落户终结的挽歌了。
但也不禁奇怪的是,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,革命本求平等的目标,忽然在一个时期内,又被阶级出身以定高低的“血统论”代替,红黑五类之分,也曾甚嚣尘上。由此不难看到,古老的已成历史垃圾的幽灵,常常于不期然中,会被人重新捡起,以“革命”的名义借尸还魂。有些深通马克思主义者,也难保脑袋里没有一丝封建残余,这也许便是老调子总唱不完的道理了。
这也无碍人们的前进步伐,现在的南京城里,不仅王谢的尊贵府邸找不到,恐怕连等级森严的朱雀桥和乌衣巷,也将随城市新建而成为史实。在这儿生活着的普通人,一定会营造自己新生活的歌,这是必然的事情。因为,每个时代总有它自己的声音,那种悖谬的陈腔老调,大概早晚要画上休止符的。









 广东顺德一酒店宰杀毒蛇 二十分钟却被断头蛇后复活咬死凶手
广东顺德一酒店宰杀毒蛇 二十分钟却被断头蛇后复活咬死凶手 日本女优让上千人任意摸胸 筹款“救地球”
日本女优让上千人任意摸胸 筹款“救地球” 实拍泰国“生猛”人妖秀 太豪放吓跑男观众
实拍泰国“生猛”人妖秀 太豪放吓跑男观众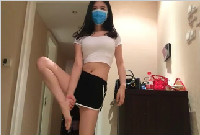 网络女主播直播“练体操” 开腿姿势太犯规
网络女主播直播“练体操” 开腿姿势太犯规 大鳄鱼竟将小鳄鱼拦腰咬成两截,恐怖血腥场面让人背后发凉!
大鳄鱼竟将小鳄鱼拦腰咬成两截,恐怖血腥场面让人背后发凉! 实拍:按摩女强行拉客到树林进行“服务”
实拍:按摩女强行拉客到树林进行“服务” 惊呆!女艺术家大街上拉男人随便摸隐私部位
惊呆!女艺术家大街上拉男人随便摸隐私部位 非洲母狮藏身动物死尸中 画面血腥令人毛骨悚然
非洲母狮藏身动物死尸中 画面血腥令人毛骨悚然 曼谷4米巨蟒吞噬成年狗难下咽又吐出(全程视频组图)
曼谷4米巨蟒吞噬成年狗难下咽又吐出(全程视频组图) 女子与情夫开房 赤身裸体的被对方原配暴踹
女子与情夫开房 赤身裸体的被对方原配暴踹 老照片:1945年日本投降十大经典画面
老照片:1945年日本投降十大经典画面 老照片:史上最著名的20幅造假照片曝光
老照片:史上最著名的20幅造假照片曝光 老照片:披露希特勒自杀现场
老照片:披露希特勒自杀现场 历史罕见瞬间
历史罕见瞬间 美国空军历史上的悲剧时刻
美国空军历史上的悲剧时刻 实拍,奥巴马搂着71岁的昂山素季瞬间
实拍,奥巴马搂着71岁的昂山素季瞬间 二战盟国的经典漫画和海报
二战盟国的经典漫画和海报 二战时美国女兵军服赏析
二战时美国女兵军服赏析 德军的“限制级”生活照
德军的“限制级”生活照 越南女兵穿比基尼给胡志明献花
越南女兵穿比基尼给胡志明献花

